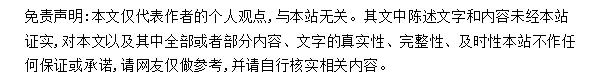“现在的原种猪很多是靠进口。这种格局必须改变,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种猪。”在2021年的全国“两会”上,全国政协委员、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再次呼吁“猪芯片”问题。他列举了“猪芯片”的九大问题,包括育种体系不完善、投入严重不足、地方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等等。
正如芯片对手机的重要性一样,“猪芯片”就是当前猪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。刘永好指出,种猪长期依靠进口,直接影响了我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的质量、速度和效益,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猪产业的发展。
种猪的脆弱性,对一些地方猪来说更为严峻。自非洲猪瘟来袭后,曲宏宇的保种场就“穿”上了层层盔甲。与全国几十个地方猪种的保种场一样,他的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也进入“战时”模式。保种场建了一圈一米五高的围墙,将场区与村庄、道路隔离开,场内的办公区、生活区与养殖区也同样用围墙隔开。曲宏宇与工作人员吃喝拉撒全在保种场里,很少出去。每天从生活区进入养殖区都要进行全身消杀、换上防护服,出来也是同样的步骤。外面的人如果想进保种场,多数只能在隔离之后进入办公区,养殖区成为禁地。
面对发病率、死亡率最高可达100%的非洲猪瘟,保种场比普通生猪场的危险要高得多。曲宏宇说,“一旦出现非洲猪瘟,从个人角度说,几年的投入都白费了;从地方猪种角度说,这个种就没了。”
急速下降的地方猪群体
曲宏宇的养猪生涯,在经历了一次灭顶之灾后,做出了路线转换。
他最初养的是外来“洋猪”,1995年,一场猪瘟袭来,一百多头外来猪全军覆没,只剩6头亲戚送的本地猪孤零零地活着。村里的长辈告诉他,活下来的是烟台黑猪,抗病性比外来猪好。
为防止再一次的全军覆没,曲宏宇开始养起了烟台黑猪。这是“逆潮流”的行为,村里人都在养外来猪,只有他养本地猪,在追求“量”的年代,注定赚不了什么钱。好的年景,能维持家里和猪场的开销,坏的时候,曲宏宇连饲料都买不起。撑不下去的时候,他曾想着连猪带场五万元卖出去,但哪怕是这个价,当时也没人愿意出。
地方猪生存之难是在短短三十年内形成的。在湖南长沙的宁乡市有句古语,“宁乡人会读书,宁乡人会养猪”,宁乡人家素有养母猪、卖仔猪的传统。该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副主任张英杰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上世纪80年代,宁乡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,也就是当地的宁乡花猪,许多人家也靠卖仔猪赚钱。而到90年代中期,随着国外的外来猪进入,宁乡花猪逐渐失去了市场份额。
这是市场行为,也是政策驱动。上世纪70年代末,我国包括猪牛羊禽等在内的每年人均肉类消费量,农民为6公斤,城镇居民为18公斤,猪肉消费在其中占80%以上。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、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随着改革开放推进,人民生活水平提升,我国的养猪市场主要开始解决量的问题,且大力推广瘦肉型猪。
因此,瘦肉率高、出栏快的外来猪,尤其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原产丹麦的长白猪、原产英国的大白猪、原产美国的杜洛克猪在国内逐渐推广开。数据对比非常明显,外来猪五六个月可以出栏,地方猪则要一年;外来猪的瘦肉率有63%~65%,地方猪则往往只有40%。对养殖户来说,投入同样的成本,养外来猪更快、卖价更高。
外来猪逐渐占据了中国市场,并形成市场占有率高达90%甚至95%的局面。中国的每年人均猪肉消费量也从上世纪70年代起逐年攀升,在2014年达最高峰41.81公斤。学界从上世纪末开始不断呼吁,应保护我国的地方猪品种。
常常找父母借钱来维持猪场运转的曲宏宇,很想知道烟台黑猪到底值不值得自己养下去。2008年,山东省畜牧业博览会在济南召开,他驱车500公里,用后备箱拉来3头特征明显的烟台黑猪参会。省畜牧兽医总站、青岛农业大学的专家们都大吃一惊,他们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血统纯正的烟台黑猪了。曲宏宇后来听说,专家们曾辗转多地寻找烟台黑猪,都无功而返,以为烟台黑猪已经灭绝。一名专家连连嘱咐他,一定要把烟台黑猪保护下去。
当时,我国的地方猪品种局面十分惨淡。“十二五”规划曾公布一组数字,我国88个地方猪品种,85%左右的群体数量呈下降趋势,31个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和濒临灭绝。过去家家户户都养猪的宁乡,本来有几十个公猪家系,但在那时仅剩下7个家系。畜牧专家循着过去仔猪外销的路径,在外市找到了3个家系,将宁乡花猪的群体恢复起来。
2010年前后,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团队曾到四川巴中市通江县的青峪乡,挨家挨户寻找当地猪种青峪猪。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朱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最终结果既让人失望,又让人庆幸。纯种青峪猪少得可怜,团队只找到了1只公猪,4只母猪,多数都已与外来猪杂交。后来,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,每年往更深的山里找寻,才陆陆续续又找回了一些青峪猪。
地方猪遗传资源保种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。自2008年起,农业农村部先后公布了七批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、保护区和保种场。截至2019年6月,共有83个地方猪种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,已建成国家级地方猪遗传资源保种场55个、保护区7个、国家家畜基因库1个,各地也建设省级地方猪保种场(区、库)80余个。
然而,扭转地方猪的惨淡局面并不容易。从“十二五”规划到“十三五”规划期间,更多的猪品种——37个猪品种处于濒危、濒临灭绝或灭绝状态,其中横泾猪、虹桥猪等8个品种已经灭绝。
另一组数据或许更加直观。四川省是生猪大省,2020年生猪出栏量达5614.4万头,位居全国第一。同时,四川也是我国的畜禽资源大省,目前共有6个地方猪品种资源。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发展处处长杨春国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从1995年到2019年,四川省地方猪数量从221.93万头减少至85.91万头。其中,农区的地方猪种在1995年、2005年以及2019年的数量分别是188.61万头、61.99万头、8.46万头。
杨春国说,两三年前,在省内针对保种场的一次座谈会上,负责人们纷纷表示,保种工作效益很低,保种场只能勉强维持。这也是国内不少保种场的现状,养地方猪并不赚钱,甚至养得越多、亏得越多。有一些保种场甚至只能将保种群体维持在政策允许的最低数,也就是100多头。如何让保种场长期运转下去,是地方猪必须解决的生存难题。
“团灭”的风险依然巨大
非洲猪瘟的来袭,让地方猪面临的局面更为艰难。朱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因市场选择,农民更愿意养收效高的外种猪,地方猪往往只能在保种场里见到。通常来说,一个地方猪种只有一个保种场,一旦保种场发现非瘟病例,按照相关规定,需整场清群,这意味着该地方猪种的“团灭”。即便不清群,一旦非瘟在保种场内发生传播,在目前国内一些保种场仅有百余头猪的情况下,地方猪的种群数量也会被影响。
当前,非洲猪瘟并没有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,对猪场来说,构建生物安全体系是唯一有效的防控手段,但中国的保种场不少都存在生物安全体系不健全的问题。朱砺介绍,保种工作讲求原产地保护,许多保种场都位置偏远,且因保种工作公益性为多,效益不佳,保种场大多规模有限,生物安全体系构建地不规范,面临非瘟的风险比规模化的养猪场更高。为此,各保种场与曲宏宇的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一样,开始构建生物安全措施。像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这样严阵以待的地方猪保种场,在中国有一百多个。
除此之外,农业农村部以及各省市还出台了一系列其他保护措施。2018年末,农业农村部提出了三公里的红线要求,即保种场周边三公里范围内,所有养猪场都要建立生物安全措施,消除风险隐患。更重视的,以湖南为例,用2000万元资金作为补贴,清退保种场及核心育种场周边三公里内的散户。
正因为“一种地方猪往往只有一个保种场”的稀缺性,各省开始不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建设备份场,将每种地方猪一分为二地保存,是最先出现的思路。杨春国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介绍,备份场的选址思路很朴素,最先考虑的就是防御距离,即备份场应足够偏远,人迹罕至,隔离封闭条件比较好。因备份场的建设需要一定时间,一些情况危急、仅有百余头存栏量的地方猪种使用了更原始的方式——将部分群体分散送往大山深处的多家农户,万一保种场清群,将来还能从农户手中收集回来,再次扩繁。
某种程度看,这不亚于一场与时间和瘟疫赛跑的抢救行动,甚至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万一保种场、备份场甚至农户散养的所有地方猪,活体保护全部失败,地方品种怎么恢复?农业农村部指出,应采集保存我国地方猪品种的遗传材料。
许多省开始布局地方猪的种质资源库,冷冻种公猪的精子、能繁母猪的卵母细胞以及胚胎。不过,朱砺指出,这三种保存方式都有其先天缺陷。精子、卵母细胞只能保留50%的遗传细胞,胚胎的获取则限于当前的技术,只能通过屠宰来进行,这无异于杀鸡取卵,对现有的地方猪种有伤害。因此,包括四川在内的一些省份在此基础上,通过体细胞采集,试验地方猪的克隆。这样,即便未来出现了活体保存团灭的最坏结果,地方猪种也有可能被恢复。
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、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楚端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作为农业农村部猪品种资源委员会专家,他尚未听说因为非瘟导致中国某种地方猪种灭绝的情况。不过,他也表示,直到现在,灭种的风险依然是巨大的,不排除未来发生的可能性。
在保种场内,地方猪的种群数量减少,已成为严峻的现实。根据我国对地方猪保种场的相关规定,为防止近交衰退,母猪应在100头以上,公猪12头以上,三代之内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猪家系数不少于6个。但从各保种场的实际情况来看,原本就种群规模偏小,公猪家系数不多。
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姜延志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从非瘟的影响来看,各地方猪保种场尽管在群体数量上通过扩群而得到了基本恢复,但从群体结构组成和遗传多样性的角度来说,其家系数和遗传多样性已遭受较大的冲击。可以肯定的是,未来,我国的地方猪存在着较大的近交衰退、品种退化的威胁。重建谱系图、厘清家系,是接下来亟须通过基因测序等现代生物科技手段来做的工作。
地方猪能占据中国人的餐桌吗?
曲宏宇的烟台黑猪有两种商业模式,一种卖做种猪,一种育肥之后,卖做商品猪。前者在非瘟之前,并无多少销路。养猪的人都清楚,养外来猪、卖外来猪更赚钱,因此,愿意买地方猪做种猪的人很少,多年来,曲宏宇的种猪也始终卖不出高价。
非瘟来袭后,这种情况才略有好转。外来猪的进口受流通限制,且许多人听说地方猪的抗疫病能力更强,因此曲宏宇的种猪销量和价格都有所增长。2020年,仅是售卖种猪,曲宏宇的流水就有几千万元,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不过,相较外来猪种在非瘟之后每头种猪上万元的定价,地方猪的种猪依然只能卖五六千元。
商品猪的销路也有限。近些年来,随着中高端消费群体对猪肉的需求从“量”转变为“质”,曲宏宇瞄准了这部分人群,建立自己的品牌,在本地售卖土猪肉。但因为养猪周期长、成本高,他的定价也高。以排骨为例,大概75元一斤,而外来猪排骨,北京新发地市场3月20日平均报价则在25元一斤。对于非一线城市来说,比普通猪肉贵一到两倍的定价使得消费群体有限。